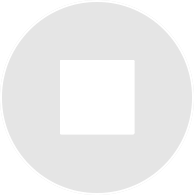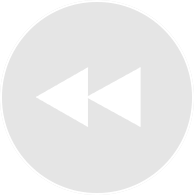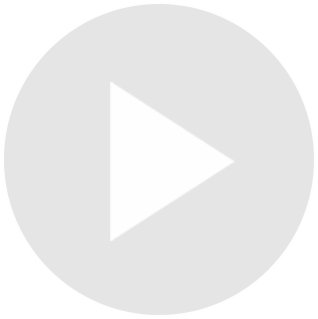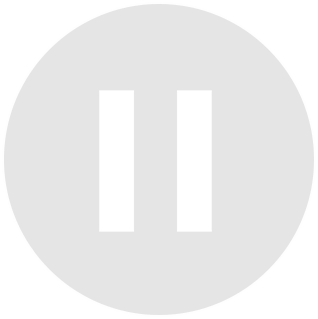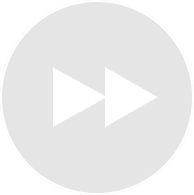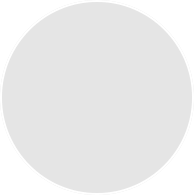雨后初晴,水面长出了长毛,有千丝万缕的白雾萦绕飞扬。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,感到肚皮和大腿突然一阵冰凉。远远看见几只野鸭,在雾气中不时出没。哗的一声,身旁冒出几圈水纹,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。
一条小船近了,船上一点红也近了,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,穿在一个女孩儿身上。女孩儿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。船头上,一个更小的男孩儿在划桨。他们各忙各的,一言不发。
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,还有这两个小小的“渔夫”。他们在远处忙碌,总是不说话,也不看我一眼。
有城里的客人要来我家,得买点儿鱼才好。于是,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:“有鱼吗?”
他们望了我一眼。
“我是说,你们有鱼卖吗?大鱼小鱼都行。”
他们仍未回话。隔了好半天,女孩儿朝这边摇了摇手。
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:“我就住在那里,有鱼就卖给我好吗?”
他们没有反应,不知是没有听清楚,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。
第二天一早,院子里传来持久的狗吠(fèi)。我来到院门口,发现那个红衣女孩儿站在门外,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,被狗吓得进退两难,赤裸(luǒ)的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。
我愣了一下,记起了昨天我在水上问购。我接过她的塑料袋,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,大的约摸半斤,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,鲫(jì)鱼、草鱼杂得有点儿不成样子。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,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。
我收下了鱼。
她走后不久,狗又叫了。窗外橘红色一晃,是她急急地返回来,跑得有点儿气喘吁吁。
“对不起,刚才错了……”她大声说。
“错了什么?”
“你们把钱算错了。”
“不会错吧?刚才是你看的秤,是你报的价,你说多少就是多少,我并没有……”
“不是,是你们们多给了。”
她红着脸说,刚才回到船上,弟弟一听钱的数字,就—口咬定她算错了,肯定没有这么多钱。他们又算了一次,发现果然多收了一块钱。
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,撩(liāo)起橘红色衣襟(jīn),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,十分复杂地打开它,又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,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一块钱,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,并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吗?“也就是一块钱,你送鱼来,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。”我说。
“不行不行……”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。
“再说,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,这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儿吧。”
“不行不行……”拨浪鼓还在摇。
她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。然而,她的小钞票凑不起一块钱。递来一张大钞票,我们又没有合适的零钱找。就这样你三我四你七我八地凑了好一阵,还是无法做到两清。最后,我满足她的要求,好歹收下了七角,并一再强调:“不要再说了,就这样算了,你再说我就不高兴了。”
她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,浑身不自在,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。
傍晚,我和妻子从外面回家,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。一位正在路边锄草的妇人说,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了,见我们不在,就把葱留在门前。
不用说,这一大把葱就是她对鱼款的补偿。
妻子叹了口气,说如今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。
我说不出话来……
每天早上,我推开窗子,发现远处的水面上总有—叶或者两叶小船,像什么人无意中遗落了一两个发夹,轻轻地别在青山绿水之中。但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。每天晚上,我走在月光下的时候,偶尔听到竹林那边还有桨声,是一条小船均匀的足迹,在水面上播出了月光的碎片,还有一个个梦境。但我依稀听得出桨声过于粗重,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。
我来到水边,发现近处根本没有船。原来是月夜太静了,仿佛缩短了声音传递的距离,远和近的动静根本无法区别。
我也不明白,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的墙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