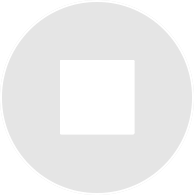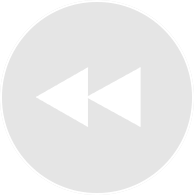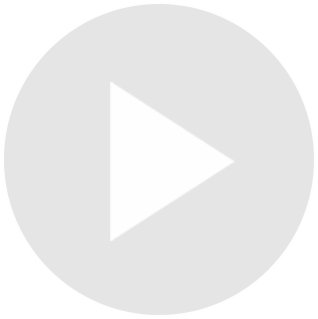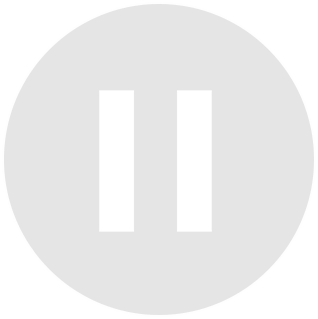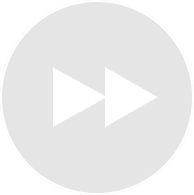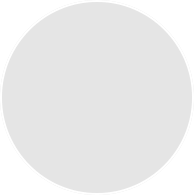做孩子的时候,盼过年的心情比大人迫切,吃穿玩乐花样都多,还可以把亲友塞到手心里的一小包压岁钱积攒起来,做个小富翁。但对孩子们来说,过年的魅力还有更深一层的缘故,便是我要写在这张纸上的。
每逢年至,小闺女们闹着戴绒花,穿红袄,嘴巴上涂上浓浓的胭脂团儿;男孩子们的兴趣都盯在鞭炮上。我则不然,最喜欢的是买个花脸戴。这是一种纸浆轧制成的面具,用渗胶的彩粉画上唱戏的那些有名有姓、威风十足的大花脸。后边拴根橡皮条儿,往头上一套,自己俨(yǎn)然就变成那员虎将了。这花脸是依脸形轧的,眼睛处挖两个孔,可以从里边往外看。但鼻子和嘴的地方不通气,一戴上,好闷,还有股臭胶和纸浆的味儿;说出话来,声音变得低而粗,却有大将威武不凡的气概,神气得很。
一年年根,舅舅带我去娘娘宫前年货集市上买花脸。过年时人都分外有劲,挤在人群里好费力。终于,我从挂满在一条横竿上的几十种花花绿绿花脸中,惊喜地发现了一个。这花脸好大,好特别!通面赤红,一双墨眉,眼角雄俊地吊起。头上边突起一块绿包头,长巾贴脸垂下,脸下边是用马尾做的很长的胡须。这花脸与那些愣头愣脑、傻头傻脑、神头鬼脸的都不一样,虽然毫不凶恶,却有股子凛然不可侵犯的庄重之气,咄咄逼人,叫我看得直缩脖子.要是把它挂在脸上,管叫别人也吓得缩脖子。我竟不敢用手指它,只是朝它扬下巴,说:“我要那个大红脸!”
卖花脸的小罗锅儿,举竿儿挑下这花脸给我,龇(zī)着黄牙笑嘻嘻地说:“还是这小少爷有眼力,要做关老爷!关老爷还得拿把青龙偃(yǎn)月刀呢!我给您挑把顶精神!”说着从戳在地上的一捆刀枪里,抽出一柄最漂亮的大刀给我。大红漆杆,金黄刀面,刀面上嵌着几块闪闪发光的小镜片,中间画一条碧绿的小龙,还拴一朵红缨子。这刀!这花脸!没想到一下子得到两件宝贝,我高兴得只是笑,话都说不出。
回家的路上,我就戴着花脸,倚着舅舅执刀而立,一路引来不少人瞧我。特别是那些与我一般大的男孩子们投来艳羡的目光时,我快活之极。舅舅给我讲了许多关公的故事——过五关斩六将、温酒斩华雄……边讲边说:“你好英雄呀!”好像在说我的光荣史。当他告我青龙偃月刀重八十斤时,我简直觉得自己力大无穷。舅舅还教我用京剧自报家门的腔调说:“我——姓关,名羽,字云长。”
到家,人人见人人夸,妈妈似乎比我更高兴。连总是厉害地板着脸的爸爸也含笑称我“小关公”。我推开大人们,跑到穿衣镜前,横刀立马地一照,呀,哪里是小关公,我是大关公哪!
这样,整个大年三十我一直戴着这花脸,谁说都不肯摘。睡觉时也戴着它,还是妈妈在我睡着后轻轻摘下放到我枕边的。转天醒来头件事就是马上戴上它,恢复我这“关老爷”的面貌。
大年初一,客人们陆陆续续来拜年,妈妈喊我去,好叫客人们见识见识我这关老爷。我手握大刀,摇晃着肩膀,威风地走进客厅,憋足嗓子叫道:“我——姓关,名羽,字云长。”
客人们哄堂大笑,都说:“好个关老爷,有你守家,保管大鬼小鬼进不来!”我越发神气,大刀呼呼抡两圈,摆个张牙舞爪的架势,逗得客人们笑个不停。
只要客人来,妈妈就喊我出场表演。妈妈还给我换上了只有拜祖宗时才能穿的那件青缎金花的小袍子。我成了全家过年的主角。连爸爸对我也另眼看待了。
我下楼一向不走楼梯。我家楼梯扶手是整根的光亮的圆木。下楼时便一条腿跨上去,“哧溜”一下滑到底。这时我就故意躲在楼上,等客人一来突然就由天而降,叫他们惊奇,效果会更棒!
下午,又有来客进入客厅,妈妈一喊我,我便跨上楼梯扶手飞骑而下,呜呀呀大叫一声闯进客厅,大刀上下一抡。谁知用力过猛,脚底没根,身子栽出去,“叭”的一声巨响,大刀正砍在花架上的大瓷瓶上,哗啦啦粉粉碎。只见瓷片、瓶里的桃枝和水飞向满屋,一块瓷片从二姑脸旁飞过,险些擦上了。屋内如淋急雨,所有人穿的新衣裳都是水渍(zì)。再看爸爸,他像老虎一样直瞪着我,哎哟,一根开花的小桃枝迎面插在他梳得油光光的头发里。后来长大才知道被我打碎的是一只祖传的乾(qián)隆官窑百蝶瓶,这简直是死罪!我坐在地上吓傻了,等候爸爸上来一顿狠狠的揪打。妈妈的神气好像比我更紧张,她一时抓不着办法救我,瞪大眼睛等待爸爸爆发。
就在这生死关头,二姑忽然破颜而笑,拍着手说道:“好啊,好啊,今年大吉大利,岁(碎)岁(碎)平安呀!哎,关老爷,干吗傻坐在地上,快起来,二姑还要看你耍大刀呢!”
谁知二姑这是使的什么法术,绷紧的气势霎(shà)时就松开了。另一位姨妈马上应和说:“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不除旧,不迎新。您等着瞧吧,今年非抱个大金娃娃不成,是吧?”她满脸欢笑朝我爸爸说,叫他应声。其他客人也一拥而上,说吉祥话,哄爸爸乐。
这些话平时根本压不住爸爸的火气,此刻竟有神奇的效力,迫使他不乐也得乐。过年乐,没灾祸。爸爸只得嘿嘿两声,点头说:“啊,好、好、好……”
尽管他脸上的笑纹明显含着被克制的怒意,我却奇迹般地因此逃脱开一次惩罚。妈妈对我丢了个眼色,我立刻爬起来,拖着大刀,狼狈而逃。身后还响着客人们着意的拍手声、叫好声和笑声。
往后几天里,再有拜年的客人来,妈妈不再喊我,节目被取消了。我躲在自己屋里很少露面,那把大刀也掖在床底下,只是依旧戴着花脸。躲在这硬纸后边,再碰到爸爸时,自己觉得有种安全感。每每从眼孔里望见爸爸阴沉含怒的脸,我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关老爷,而是个可怜虫了!
过了正月十五,大年就算过完了。我因为和妹妹争吃糖瓜,被爸爸提腰抓起来,按在床上死揍一顿。盛怒下,他向我要去那把惹祸的大刀,用力折成几段,大花脸也撕成碎片片。我心里清楚,他把我打碎花瓶的罪过加在这件事上一起清算了。
从这事,我悟到一个祖传的经验:一年之中唯有过年这几天是孩子们的自由日,在这几天里无论怎样放胆去闹,也不会立刻得到惩罚。这便是所有孩子都盼望过年的更深一层的缘故。当然那被撕碎的花脸也提醒我,在这有限的自由里可得勒着点自己,当心事后加倍算账。